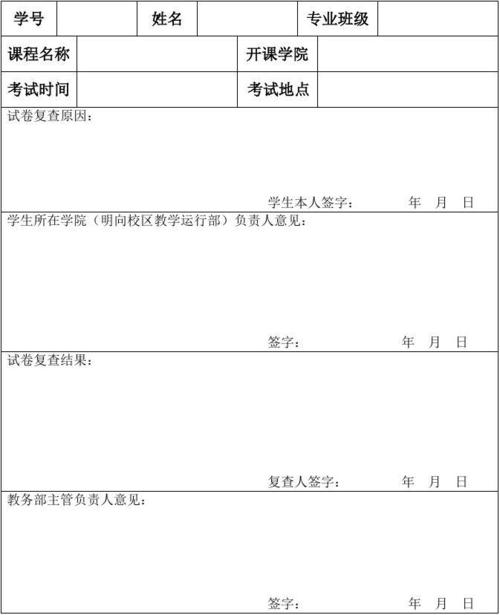现代大学英语精读4-第一课翻译
四川一本线-常识判断题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译
4-第一课翻
Thinking as a Hobby
思考作为一种嗜好
还是个孩
子的时候我就得出了思考分三种等级
的结论。后来思考成了嗜好,我进而得出了一个
更加离奇的
结论,那就是:我自己根本不会思考。
那个时候我一定是个很让大人头疼的小孩。当然我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了,
但却记得他们一开始在我眼中就是如何不可理
喻的。第一个把思考这个问题带到我面前的是我
文法学校的校长,当然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结果
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些小雕像,
就在他书桌后面一个高高的橱柜上面。其中一位
女士除了一条浴巾外一丝不挂。她好象被永远地
冻结在对浴巾再往下滑的恐惧中了。而不幸的是
她没有手臂,所以无法把浴巾拉上来。在她的身
边蜷伏着一头美洲豹,好象随时都会往下跳到档
案橱柜最上层的抽屉上去,我懵懵懂懂地把那个
抽屉上标着的理解成为猎物临死前绝望
的哀鸣
惨叫。在豹子的另一边端坐着一个健硕
的裸体男子,他手肘支在膝头,手握拳托着腮帮
<
br>
子,全然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过了一些时候,我对这些雕像有了一些了
解,才
知道把它们放在正对着犯错的孩子的位置是因
为对校长来说这些雕像象征着整个生命。那
位裸
体的女士是米洛斯的维纳丝。她象征着爱。她不
是在为浴巾担心,而是忙着显示美丽。美洲
豹象
征着自然,它在那里显得很自然而已。那位健硕
的裸体男子并不痛苦,他是洛丁的思索者,
一个
纯粹思索的象征。要买到表达生活在你心中的意
义的小石膏像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想我得解释一下,我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为
我最近做过或者没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我
是不堪教化的。其实应该说,我是顽劣不羁,头
脑迷糊的。大人们从来不讲道理。每次在校长桌
前接受处罚,那些雕像在他上方白晃晃地耀眼
时,我就会垂下头,在身后紧扣双手,两只鞋不<
br>停地蹭来蹭去。
校长透过亮晶晶的眼镜片眼神暗淡地看着我,:
“我们该拿你怎么办呢?”
哦,他们要拿我怎么办呢?我盯着旧地毯更狠命
地蹂躏我的鞋。
“抬起头来,孩子!你就不能抬起头来吗?”
然后我就会抬起头来看橱
柜,看着裸体女士被冻
结在恐惧中,健硕的男子无限忧郁地凝视着猎豹
的后腿。我跟校长没什么
好说的。他的镜片反光,
所以我看不到镜片后面有什么人性的东西,所以
没有交流的可能。
“你从来都不动脑筋思考的吗?”
不,我不思考,刚才没思考,也不会思考——我
只是在痛苦地等待接见结束。
“那你最好学一学 —— 你学了吗?”
有一次,校长跳起身来伸手取下洛丁的杰作重重
地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一个人真正在思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我毫无兴趣地看了看桌上的男子,什么也没弄
懂。
“回你班上去。”
显然我是缺了点什么。大自然赋予其余的所有的
人第六感觉却独独漏掉了
我。一定是这样的,在
回班上去的路上我想着。因为无论我是打烂了玻
璃窗,不记得波义耳法则
,还是上学迟到了,我
的老师们都会千篇一律地得出一个答案:“你为
什么不会思考呢?”
要我说,我打碎了玻璃窗是因为我想用板球打杰
克.阿尼没打着;我记不住波义耳法
则是因为我
根本没想去记;迟到了是因为我更喜欢在桥上看
河水。事实上,我是邪恶的。难道我
的老师们是
那么的善良,以致于无法理解我的堕落深度?他
们是那种心地清澈,不受折磨,凭那
神秘的思考
指导每一个行动的人?整件事情都是让人无法
理解的。更
小一点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思索者塑
像也是令人迷惑的。我才不相信我的哪位老师思
考的时候是
不穿衣服的。我象那些生来耳聋却决
意苦苦寻求声音的人一样观察着我的老师们,想
要了解思想
。
那时有位豪顿先生,他总是要我思考。他带着谦
逊的满足告诉我他自己就动过一
点脑筋思索过。
那么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酗酒?莫非酗酒其
实比外表看起来更有意义?而如果
不是这样,酗
酒事实上损害健康 —— 豪格先生无疑被酒毁
了的 —— 那他为什么还成天谈
论纯净的生活
以及新鲜空气的好处?他一边说一边还会象一
位常年在山峦间行走的人那样伸开双
臂,说:
“新鲜空气对我有好处,孩子们 —— 我知道
的!”
有时候讲到兴头上,他会从讲台上跳下来,把我
们一窝蜂地赶到外头去。
“现在,孩子们!深呼吸!感觉上帝创造的美好
气流直接进入你们的体内!”
他会站在我们面前,为他的健康而欣喜,好象他
一个常进行户外活动的人。他会叉着腰,深深地吸一口气。你能听到风被他的胸腔堵住,遇到障
碍物艰难前进发出的声音。他的身体因为不习惯这样的感觉而摇摇晃晃,脸色变得惨白。他会步
履蹒跚地走回讲台,然后瘫软在那里,一个上午都缓不过劲来 。
豪顿先生喜欢发表关于美好的、清心寡欲、尽职
尽责生活的
独白。但是在发表这些独白的间隙,
如果有个女孩经过窗前,灵巧的小脚发出轻轻的
脚步声。他
就会停下他的演讲,脖子不由自主地
扭转过去,一直目送她走出视线之外。在这种情
况下,我认
为他不是受思想,而是受他后颈里某
个看不到却无法抗拒的发条的控制。
我对于他
的脖子十分感兴趣。通常它在领口上方
稍稍凸出。但是豪顿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
经和美国
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而且——由于谁
也弄不懂的逻辑 —— 对两个国家都
深恶痛绝。
无论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在时事中表现突出,他
都对它没有好感,任何论证都无法说
服他。他会
捶着桌子,脖子胀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他会叫道:“但是我已经想过这个问
题了,而且
我知道我想什么!”
豪顿先生用他的脖子思考。
还有帕森小姐。她要我们相信她最大的愿望是希
望我们幸福,但是即使是那个时候凭着我小孩子
神秘的的直觉我都知道,她最希望得到的是她从
未得到过的丈夫。还有汉兹先生 —— 等等。
我要对我的老师们进行详细的分析是为了介绍
一下通常被称为思想的本质。通过他们
我发现思
考通常是充满了无意识的偏见、无知和虚伪的。
在训诫无私的纯真的时候它的脖子却为
了短裙
而执意扭曲。从技术上而言,它娴熟如同商人玩
高尔夫,诚实如同政客的意图,或者
——更接
近我自己的领域——
有条理如同大多数写出来
的书。这就是后来被我称作第三等级的思考,虽
然事实上称它为感觉更为恰当。
诚然,偏见里是有无辜的成分,但是在那时我对<
br>第三等级的思考的态度是毫不宽容的蔑视和不
假思索的嘲笑。我以驳斥一位憎恨德国人却主张爱我们的敌人的虔诚女士为乐。她让我懂得了和
第三等级思考者打交道的一个重大的真理。因为她,我不再轻易地拒绝百分之九十的人可能经历
过的精神过程。他们高度地团结一致。我们最好尊重他们,因为我们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势单
力薄。一大堆第三等级的思考者,众口一词,籍着自己的偏见温暖双手,他们是不会感激你指出
他们信仰中的矛盾的。人是一种爱群居的动物,就象牛喜欢沿着山坡的同一条道路吃草一样喜
爱共识。
第二个等级的思考是对
于矛盾的觉察。难倒那位
可怜而虔诚的老太太的时候我达到了这个层次。
第二等级的思考者虽然
常常回会犯另一个错,落
在后面,但他们不会轻易地被吓倒。第二等级思
考是一种警醒状态下的
退缩。这种思考成为我的
嗜好,给我带来满足干的同时也带来孤独感。因
为第二等级思考具有破坏却没有创造的能力。它
让我在冷眼看着人群为国王陛下欢呼的时候觉
得这样的喧嚣不知所谓,却没有提供什么可以替
代这样强烈爱国精神。但是这样的思考还是有好
处的。听人们以狐狸喜欢这样的待遇为理由为他
们捕猎狐狸,把它们撕成碎片的习惯辩护,我们
的女首相谈论通过逮捕尼赫鲁和甘地这样的人
跟印度协商的好处,美国政客们可以刚谈完和平
转身就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时候,是的,还是有
令人高兴的时刻的。
但是,当我渐
渐长大,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不得
不承认豪顿先生不是唯一一个无法抗拒脖子里
的发条的人。我
也一样感觉到了强大的自然之手
的力量,开始发现指出矛盾有可能代价昂贵,也
可能是有趣的。
比如说,曾经有个严肃而迷人的
姑娘,她的名字叫露丝。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无神
论者。第二等级
的思考对于宗教来说是一种威
胁,象九柱游戏里的小柱一样把宗教流派各个击
破。我象个第三等
级的思考者一样假惺惺地任由
她改变我的信仰。她是一个卫理会会派教徒
——
至少,她父母是,因此而露丝也得是。但
是,呵呵,露丝没有用圣灵的精神来
转化我,而
是愚蠢地用她可爱的小嘴试图说服我。她声称圣
经(詹姆士国王版)逐字逐句都是得
到启示而来
的。我反驳说天主教徒信仰圣杰罗姆的拉丁文圣
经,而这两本书是不同的。争论顿时
卡壳了。
最后她说有那么多卫理会会派教徒,他们不可能
是错的,几百万的人都错
了,可能吗?这太简单
了,我倔强地说(你越接近露丝,她就越好接近),
罗马天主教徒也为数
众多,他们也不可能是错
的,他们有几亿人,可能都错了吗?她眼中扑闪
着疑虑。我伸手揽过她
的腰屏住呼吸低声说,如
果算人数,我该捐钱给佛教徒。露丝的确是为我
好,因为我人这么好。
但是我的手臂加上那些数
不胜数的佛教徒实在让她无法忍受了。
那天晚上,她父亲
来拜访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副
面红耳赤,义愤填膺的样子。我为发生过的事情
受到了盘问。幸好
我们当时都才十四岁。我失去
了露丝,却冤枉地担上了准浪子的名声。
所以第二等级思考可能会是危险的。我记得我是
在十五岁的时候了解
到了这一点后从第二等级
的高度对第三等级的局限性作出了一番评论。一
天晚上,我一个人来到
学校的礼堂为一个聚会做
准备。校长室的门是开着的。我走了进去。校长
已经不再把洛丁的思考
者重重地板在桌上作为
年轻人的榜样了。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多的
侯选者,那些雕像还在老
地方,在那橱柜顶上白
晃晃的落满尘埃。我站在一把椅子上把他们进行
了重新的排列。我把披着
浴巾的维纳斯放在档案
橱柜上,这样顶层抽屉就接住了她在性感的骚动
中发出的喘息:“A-a
h!”那个怪异的思考者,我
把它放到了橱柜边缘,这样他好象在朝下盯着那
条浴巾,等待着它
掉下来。
第二等级思考虽然让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兴奋,却
无法令人满足。寻找比我
们年长的人的缺陷助长
了年轻的自我,却无法让人觉得安全。我发现第
二等级不仅是指出矛盾的
力量。它带着游泳者离
开岸游了一段距离,然后把他留在那里,束手无
策。我判定本丢.彼拉多
就是典型的第二等级思
考者。“什么是真理?”他问道,一种十分常见却
总出现在争论的末尾而
不是开头的第二等级思
考m
67。还有更高一级的思索问过“什么是真
理?”后就开始去寻找它。
但这些第一
等级思考者是十分罕见的。他们没有
亲自来我的文法学校但却藏在书籍里。我向往他
们是因为我
雄心勃勃,因为我现在发现自己的嗜
好如果不能更进一步就不能令人满意。如果你出
发去爬山,
不论你爬了多高,只要没到顶就不算
成功。
在牛津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真的碰
到过一
个第一等级的思考者。当时我在麦格德林鹿公园
的一座小桥上往下看。一个小个子蓄着胡
子戴着
帽子的人走过来站到我身边。他是从纳粹德国逃
到牛津来暂时避难的,他的名字是爱因斯
坦。
但那个时候爱因斯坦教授还不懂英文,而我只知
道德文的几个单词。我向他微
笑,想以这样无声
的方式向他传达所有英国人对他的友爱和尊敬。
有可能——我得承认 ——我
觉得此刻是两个第
一等级思考者肩并肩站着。然而我怀疑我的表情
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无形的
敬畏。我愿意用我
懂得的希腊语、拉丁文、法语和大部分的英语来
换
取足够的德语来跟他交流。可是我们却咫尺天
涯,他象我的校长一样不可理解。我们一块在桥
上
站了大约五分钟,不可否认是作为一个第一等
级思考者和心情激动的景仰者。真不愧是伟人,
爱
因斯坦教授意识到任何联系都比没有好。指着
河里游动着的一条鲑鱼。
他说:“鱼。”
我的头脑一阵晕眩。我在这里,和伟人并肩,却
和真正的第三等级思考者一样无助。
我拼命想作
出点表示,告诉他我也一样尊重纯粹的推理。我
不住地点头。然后忽然灵光乍现,我
用掉了我一
半的德语词汇说道“鱼,是的,是的。”
我们肩并肩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爱因斯坦教授
飘然而去, 身形间仍然洋溢着善意和亲切。
我也可以成为第一等级思考者的。即使在人生最
得意的时候我也是心无挂碍的。政治
和宗教系
统、社会风俗、忠诚和传统,都象腐烂的苹果纷
纷从树上掉落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嗜
好,板球
的明智替代品,因为你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思
考。最后我想
出了为第一等级思考辩护永远的理
由:它的标志、印记和章程。我设计了一个连贯
的生活体系。
这是一个道德体系,完全合乎逻辑
的道德体系。当然,我很乐意承认,要世界按我
的思考方式转
化将是困难的,因为我的体系废除
了诸如大公司、中央政府、军队、婚姻等等之类
的琐事。
又是露丝的问题。我曾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站在
我这边,他们现在仍然站在我这边。
但是我的熟
人都不见了,带着他们的女孩子消失了。姑娘们
好象对世界的现状出奇的满意。她们
用一只戒指
来衡量那个毫无意义的仪式。小伙子一方面愿意
对婚姻带来的一连串可悲的后果让步
,同时也舍
不得放弃有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份事业的组织机
构。有一个在皇家海军当下等兵的年轻
人,对于
不要大公司和婚姻乐意之至,但是一听我提议要
一个没有战舰的世界时他的脖子跟豪顿
先生一
样胀得通红。
游戏太过火了?它还是游戏吗?在战前的那段
日子,为了这个嗜好我固执地失去了很多东西。
现在你一定指望我描述我如何认识
到了我自己
路线的荒谬回到温暖的小巢了吧,回到那偏见常
常被称为忠诚,无谓的行为因为重复
被神圣化为
风俗的小巢里,满足于把感觉说成思考。
但是,你错了。我把我的嗜好变成了职业。
如果我还回到校长室里而那些雕像还在
那里,我
会重新安排它们的位置。我会掸掉维纳斯身上的
灰尘,因为我已经了解她美好的本质,
开始喜爱
她了。但是我会把陷入沉思的思考者放到背光的
位置,而在他身后,放上那头蜷伏着准
备扑上来
的美洲豹。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
译
4-第一课翻
Thinking as a Hobby
思考作为一种嗜好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得出了思考分三种等级
的结论。
后来思考成了嗜好,我进而得出了一个
更加离奇的结论,那就是:我自己根本不会思考。
<
br>那个时候我一定是个很让大人头疼的小孩。当然
我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样子了,<
br>但却记得他们一开始在我眼中就是如何不可理
喻的。第一个把思考这个问题带到我面前的是我文法学校的校长,当然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结果
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些小雕像,就在他书桌后面一个高高的橱柜上面。其中一位
女士除了一条浴巾外一丝不挂。她好象被永远地冻结在对浴巾再往下滑的恐惧中了。而不幸的是
她没有手臂,所以无法把浴巾拉上来。在她的身边蜷伏着一头美洲豹,好象随时都会往下跳到档
案橱柜最上层的抽屉上去,我懵懵懂懂地把那个抽屉上标着的理解成为猎物临死前绝望
的哀鸣惨叫。在豹子的另一边端坐着一个健硕
的裸体
男子,他手肘支在膝头,手握拳托着腮帮
子,全然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过了一些时候,我对这些雕像有了一些了解,才
知道把它们放在正对着犯错的孩子的
位置是因
为对校长来说这些雕像象征着整个生命。那位裸
体的女士是米洛斯的维纳丝。她象征着
爱。她不
是在为浴巾担心,而是忙着显示美丽。美洲豹象
征着自然,它在那里显得很自然而已。
那位健硕
的裸体男子并不痛苦,他是洛丁的思索者,一个
纯粹思索的象征。要买到表达生活在你
心中的意
义的小石膏像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想我得解释一下,我是校长办公室的常
客,为
我最近做过或者没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我
是不堪教化的。其实应该说,我是顽劣不
羁,头
脑迷糊的。大人们从来不讲道理。每次在校长桌
前接受处罚,那些雕像在他上方白晃晃地
耀眼
时,我就会垂下头,在身后紧扣双手,两只鞋不
停地蹭来蹭去。
校长透过亮晶晶的眼镜片眼神暗淡地看着我,:
“我们该拿你怎么办呢?”
哦,他们要拿我怎么办呢?我盯着旧地毯更狠命
地蹂躏我的鞋。
“抬起头来,孩子!你就不能抬起头来吗?”
然后我就会抬起头来看橱
柜,看着裸体女士被冻
结在恐惧中,健硕的男子无限忧郁地凝视着猎豹
的后腿。我跟校长没什么
好说的。他的镜片反光,
所以我看不到镜片后面有什么人性的东西,所以
没有交流的可能。
“你从来都不动脑筋思考的吗?”
不,我不思考,刚才没思考,也不会思考——我
只是在痛苦地等待接见结束。
“那你最好学一学 —— 你学了吗?”
有一次,校长跳起身来伸手取下洛丁的杰作重重
地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一个人真正在思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我毫无兴趣地看了看桌上的男子,什么也没弄
懂。
“回你班上去。”
显然我是缺了点什么。大自然赋予其余的所有的
人第六感觉却独独漏掉了
我。一定是这样的,在
回班上去的路上我想着。因为无论我是打烂了玻
璃窗,不记得波义耳法则
,还是上学迟到了,我
的老师们都会千篇一律地得出一个答案:“你为
什么不会思考呢?”
要我说,我打碎了玻璃窗是因为我想用板球打杰
克.阿尼没打着;我记不住波义耳法
则是因为我
根本没想去记;迟到了是因为我更喜欢在桥上看
河水。事实上,我是邪恶的。难道我
的老师们是
那么的善良,以致于无法理解我的堕落深度?他
们是那种心地清澈,不受折磨,凭那
神秘的思考
指导每一个行动的人?整件事情都是让人无法
理解的。更
小一点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思索者塑
像也是令人迷惑的。我才不相信我的哪位老师思
考的时候是
不穿衣服的。我象那些生来耳聋却决
意苦苦寻求声音的人一样观察着我的老师们,想
要了解思想
。
那时有位豪顿先生,他总是要我思考。他带着谦
逊的满足告诉我他自己就动过一
点脑筋思索过。
那么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酗酒?莫非酗酒其
实比外表看起来更有意义?而如果
不是这样,酗
酒事实上损害健康 —— 豪格先生无疑被酒毁
了的 —— 那他为什么还成天谈
论纯净的生活
以及新鲜空气的好处?他一边说一边还会象一
位常年在山峦间行走的人那样伸开双
臂,说:
“新鲜空气对我有好处,孩子们 —— 我知道
的!”
有时候讲到兴头上,他会从讲台上跳下来,把我
们一窝蜂地赶到外头去。
“现在,孩子们!深呼吸!感觉上帝创造的美好
气流直接进入你们的体内!”
他会站在我们面前,为他的健康而欣喜,好象他
一个常进行户外活动的人。他会叉着腰,深深地吸一口气。你能听到风被他的胸腔堵住,遇到障
碍物艰难前进发出的声音。他的身体因为不习惯这样的感觉而摇摇晃晃,脸色变得惨白。他会步
履蹒跚地走回讲台,然后瘫软在那里,一个上午都缓不过劲来 。
豪顿先生喜欢发表关于美好的、清心寡欲、尽职
尽责生活的
独白。但是在发表这些独白的间隙,
如果有个女孩经过窗前,灵巧的小脚发出轻轻的
脚步声。他
就会停下他的演讲,脖子不由自主地
扭转过去,一直目送她走出视线之外。在这种情
况下,我认
为他不是受思想,而是受他后颈里某
个看不到却无法抗拒的发条的控制。
我对于他
的脖子十分感兴趣。通常它在领口上方
稍稍凸出。但是豪顿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
经和美国
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而且——由于谁
也弄不懂的逻辑 —— 对两个国家都
深恶痛绝。
无论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在时事中表现突出,他
都对它没有好感,任何论证都无法说
服他。他会
捶着桌子,脖子胀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他会叫道:“但是我已经想过这个问
题了,而且
我知道我想什么!”
豪顿先生用他的脖子思考。
还有帕森小姐。她要我们相信她最大的愿望是希
望我们幸福,但是即使是那个时候凭着我小孩子
神秘的的直觉我都知道,她最希望得到的是她从
未得到过的丈夫。还有汉兹先生 —— 等等。
我要对我的老师们进行详细的分析是为了介绍
一下通常被称为思想的本质。通过他们
我发现思
考通常是充满了无意识的偏见、无知和虚伪的。
在训诫无私的纯真的时候它的脖子却为
了短裙
而执意扭曲。从技术上而言,它娴熟如同商人玩
高尔夫,诚实如同政客的意图,或者
——更接
近我自己的领域——
有条理如同大多数写出来
的书。这就是后来被我称作第三等级的思考,虽
然事实上称它为感觉更为恰当。
诚然,偏见里是有无辜的成分,但是在那时我对<
br>第三等级的思考的态度是毫不宽容的蔑视和不
假思索的嘲笑。我以驳斥一位憎恨德国人却主张爱我们的敌人的虔诚女士为乐。她让我懂得了和
第三等级思考者打交道的一个重大的真理。因为她,我不再轻易地拒绝百分之九十的人可能经历
过的精神过程。他们高度地团结一致。我们最好尊重他们,因为我们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势单
力薄。一大堆第三等级的思考者,众口一词,籍着自己的偏见温暖双手,他们是不会感激你指出
他们信仰中的矛盾的。人是一种爱群居的动物,就象牛喜欢沿着山坡的同一条道路吃草一样喜
爱共识。
第二个等级的思考是对
于矛盾的觉察。难倒那位
可怜而虔诚的老太太的时候我达到了这个层次。
第二等级的思考者虽然
常常回会犯另一个错,落
在后面,但他们不会轻易地被吓倒。第二等级思
考是一种警醒状态下的
退缩。这种思考成为我的
嗜好,给我带来满足干的同时也带来孤独感。因
为第二等级思考具有破坏却没有创造的能力。它
让我在冷眼看着人群为国王陛下欢呼的时候觉
得这样的喧嚣不知所谓,却没有提供什么可以替
代这样强烈爱国精神。但是这样的思考还是有好
处的。听人们以狐狸喜欢这样的待遇为理由为他
们捕猎狐狸,把它们撕成碎片的习惯辩护,我们
的女首相谈论通过逮捕尼赫鲁和甘地这样的人
跟印度协商的好处,美国政客们可以刚谈完和平
转身就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时候,是的,还是有
令人高兴的时刻的。
但是,当我渐
渐长大,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不得
不承认豪顿先生不是唯一一个无法抗拒脖子里
的发条的人。我
也一样感觉到了强大的自然之手
的力量,开始发现指出矛盾有可能代价昂贵,也
可能是有趣的。
比如说,曾经有个严肃而迷人的
姑娘,她的名字叫露丝。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无神
论者。第二等级
的思考对于宗教来说是一种威
胁,象九柱游戏里的小柱一样把宗教流派各个击
破。我象个第三等
级的思考者一样假惺惺地任由
她改变我的信仰。她是一个卫理会会派教徒
——
至少,她父母是,因此而露丝也得是。但
是,呵呵,露丝没有用圣灵的精神来
转化我,而
是愚蠢地用她可爱的小嘴试图说服我。她声称圣
经(詹姆士国王版)逐字逐句都是得
到启示而来
的。我反驳说天主教徒信仰圣杰罗姆的拉丁文圣
经,而这两本书是不同的。争论顿时
卡壳了。
最后她说有那么多卫理会会派教徒,他们不可能
是错的,几百万的人都错
了,可能吗?这太简单
了,我倔强地说(你越接近露丝,她就越好接近),
罗马天主教徒也为数
众多,他们也不可能是错
的,他们有几亿人,可能都错了吗?她眼中扑闪
着疑虑。我伸手揽过她
的腰屏住呼吸低声说,如
果算人数,我该捐钱给佛教徒。露丝的确是为我
好,因为我人这么好。
但是我的手臂加上那些数
不胜数的佛教徒实在让她无法忍受了。
那天晚上,她父亲
来拜访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副
面红耳赤,义愤填膺的样子。我为发生过的事情
受到了盘问。幸好
我们当时都才十四岁。我失去
了露丝,却冤枉地担上了准浪子的名声。
所以第二等级思考可能会是危险的。我记得我是
在十五岁的时候了解
到了这一点后从第二等级
的高度对第三等级的局限性作出了一番评论。一
天晚上,我一个人来到
学校的礼堂为一个聚会做
准备。校长室的门是开着的。我走了进去。校长
已经不再把洛丁的思考
者重重地板在桌上作为
年轻人的榜样了。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找到更多的
侯选者,那些雕像还在老
地方,在那橱柜顶上白
晃晃的落满尘埃。我站在一把椅子上把他们进行
了重新的排列。我把披着
浴巾的维纳斯放在档案
橱柜上,这样顶层抽屉就接住了她在性感的骚动
中发出的喘息:“A-a
h!”那个怪异的思考者,我
把它放到了橱柜边缘,这样他好象在朝下盯着那
条浴巾,等待着它
掉下来。
第二等级思考虽然让生活充满了乐趣和兴奋,却
无法令人满足。寻找比我
们年长的人的缺陷助长
了年轻的自我,却无法让人觉得安全。我发现第
二等级不仅是指出矛盾的
力量。它带着游泳者离
开岸游了一段距离,然后把他留在那里,束手无
策。我判定本丢.彼拉多
就是典型的第二等级思
考者。“什么是真理?”他问道,一种十分常见却
总出现在争论的末尾而
不是开头的第二等级思
考m
67。还有更高一级的思索问过“什么是真
理?”后就开始去寻找它。
但这些第一
等级思考者是十分罕见的。他们没有
亲自来我的文法学校但却藏在书籍里。我向往他
们是因为我
雄心勃勃,因为我现在发现自己的嗜
好如果不能更进一步就不能令人满意。如果你出
发去爬山,
不论你爬了多高,只要没到顶就不算
成功。
在牛津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真的碰
到过一
个第一等级的思考者。当时我在麦格德林鹿公园
的一座小桥上往下看。一个小个子蓄着胡
子戴着
帽子的人走过来站到我身边。他是从纳粹德国逃
到牛津来暂时避难的,他的名字是爱因斯
坦。
但那个时候爱因斯坦教授还不懂英文,而我只知
道德文的几个单词。我向他微
笑,想以这样无声
的方式向他传达所有英国人对他的友爱和尊敬。
有可能——我得承认 ——我
觉得此刻是两个第
一等级思考者肩并肩站着。然而我怀疑我的表情
所传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无形的
敬畏。我愿意用我
懂得的希腊语、拉丁文、法语和大部分的英语来
换
取足够的德语来跟他交流。可是我们却咫尺天
涯,他象我的校长一样不可理解。我们一块在桥
上
站了大约五分钟,不可否认是作为一个第一等
级思考者和心情激动的景仰者。真不愧是伟人,
爱
因斯坦教授意识到任何联系都比没有好。指着
河里游动着的一条鲑鱼。
他说:“鱼。”
我的头脑一阵晕眩。我在这里,和伟人并肩,却
和真正的第三等级思考者一样无助。
我拼命想作
出点表示,告诉他我也一样尊重纯粹的推理。我
不住地点头。然后忽然灵光乍现,我
用掉了我一
半的德语词汇说道“鱼,是的,是的。”
我们肩并肩站了大约五分钟。然后爱因斯坦教授
飘然而去, 身形间仍然洋溢着善意和亲切。
我也可以成为第一等级思考者的。即使在人生最
得意的时候我也是心无挂碍的。政治
和宗教系
统、社会风俗、忠诚和传统,都象腐烂的苹果纷
纷从树上掉落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嗜
好,板球
的明智替代品,因为你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思
考。最后我想
出了为第一等级思考辩护永远的理
由:它的标志、印记和章程。我设计了一个连贯
的生活体系。
这是一个道德体系,完全合乎逻辑
的道德体系。当然,我很乐意承认,要世界按我
的思考方式转
化将是困难的,因为我的体系废除
了诸如大公司、中央政府、军队、婚姻等等之类
的琐事。
又是露丝的问题。我曾有一些很要好的朋友站在
我这边,他们现在仍然站在我这边。
但是我的熟
人都不见了,带着他们的女孩子消失了。姑娘们
好象对世界的现状出奇的满意。她们
用一只戒指
来衡量那个毫无意义的仪式。小伙子一方面愿意
对婚姻带来的一连串可悲的后果让步
,同时也舍
不得放弃有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份事业的组织机
构。有一个在皇家海军当下等兵的年轻
人,对于
不要大公司和婚姻乐意之至,但是一听我提议要
一个没有战舰的世界时他的脖子跟豪顿
先生一
样胀得通红。
游戏太过火了?它还是游戏吗?在战前的那段
日子,为了这个嗜好我固执地失去了很多东西。
现在你一定指望我描述我如何认识
到了我自己
路线的荒谬回到温暖的小巢了吧,回到那偏见常
常被称为忠诚,无谓的行为因为重复
被神圣化为
风俗的小巢里,满足于把感觉说成思考。
但是,你错了。我把我的嗜好变成了职业。
如果我还回到校长室里而那些雕像还在
那里,我
会重新安排它们的位置。我会掸掉维纳斯身上的
灰尘,因为我已经了解她美好的本质,
开始喜爱
她了。但是我会把陷入沉思的思考者放到背光的
位置,而在他身后,放上那头蜷伏着准
备扑上来
的美洲豹。